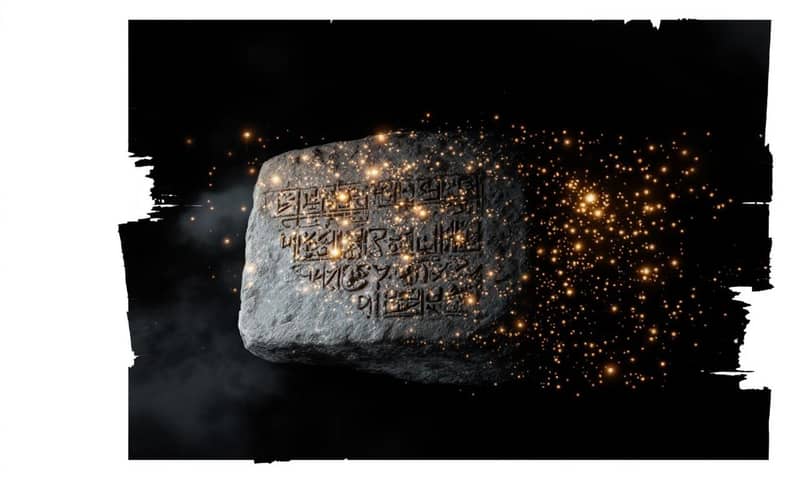欸,我們是怎麼開始「相信」Google給的第一個答案的?
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,但有時候我會突然懷念以前「找資料」的方式。對,就是那個還要自己動腦的年代。你可能會開個五、六個分頁,標題一個個看,然後像偵探一樣拼湊出「嗯,這個來源好像比較可信」的結論。
那過程...說真的,不完美,但很有用。你不只是在找資訊,你其實是在學怎麼「判斷」資訊。但現在呢?答案直接就貼在最上面,一個框框,漂漂亮亮的。
我們好像不再需要去「瀏覽」資訊了,我們變成在跟它「談判」。這是我最近一直在想的一件事,搜尋這件事,已經變成一場關於「真實」的談判。而且,你知道嗎,任何談判的結果,重點從來不只是講了什麼,更重要的是...它是「怎麼被呈現」的。
剛好最近讀到一個快被遺忘的理論,來自一個叫哈羅德·伊尼斯 (Harold Innis) 的人,他幾十年前的想法,沒想到 perfectly 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現在會陷入這種跟 AI 答案「協商真實性」的窘境。
一句話結論
搜尋引擎從「幫你找資料的工具」變成「直接給你答案的權威」,這徹底改變了我們建立信任的方式,品牌如果還在玩以前的 SEO 關鍵字遊戲,很快就會發現沒人相信你了。
為什麼「傳遞方式」比內容還重要?
OK,所以這位伊尼斯先生,他在大概...嗯,20 世紀中吧,他就在研究一個蠻酷的問題:為什麼有些知識可以流傳好幾個世紀,有些卻一下子就消失了?他的答案超簡單,卻又很有道理:因為資訊的「傳遞媒介」本身就帶有偏見。
不過他講的「媒體偏誤」(Media Bias),跟你我想的政治立場那種不一樣。他指的是一種「結構性」的偏誤。每種媒介——石頭、紙、廣播、甚至是現在的 AI——天生就會讓「真實」往某個方向傾斜。
他把媒介分成兩大類,我覺得這個分類到現在還是超實用:
時間偏誤 vs. 空間偏誤的媒體
這聽起來有點學術,但其實很好懂。你想想看,在石頭上刻字,跟用 LINE 傳訊息,這兩件事的「感覺」就完全不同。
| 特性 | 時間偏誤的媒體 (Time-biased) | 空間偏誤的媒體 (Space-biased) |
|---|---|---|
| 主要目標 | 讓資訊「跨越世代」。就是要流傳千年,給孫子的孫子看。 | 讓資訊「跨越距離」。現在、立刻、馬上讓另一邊的人知道! |
| 感覺像是... | 在石碑上刻字、口述歷史、蓋一座紀念碑。很慢、很重、很莊嚴。 | 報紙、廣播、Email、社群貼文...還有,現在的 AI 答案。超快、超輕、超容易複製。 |
| 犯錯的代價 | 高到嚇死人。你想想,字刻上石頭就改不掉了耶,你敢亂寫嗎? | 幾乎是零。廣播講錯了,明天道歉就好。AI 答錯了...嗯,它下一秒就換個答案給你了。 |
| 培養出的文化 | 重視記憶、傳統、和穩定。所有事都慢慢來,想清楚再做。 | 重視速度、擴張、和當下。求新求變,昨天的事就是舊聞。 |
伊尼斯當時就很擔心,如果一個文明太過於偏向「空間偏誤」,也就是瘋狂追求速度和擴散,那「記憶」就會成為犧牲品。當速度變成唯一目標,所有的「摩擦力」——像是查證、思考、辯論——都會消失。
當這些摩擦力消失,信念就形成的太輕易了。這就有點恐怖了。
人們會開始相信一些事情,但卻想不起來當初為什麼相信。資訊滿天飛,每個人好像什麼都懂一點,但沒有一件事是懂得到足以產生堅定的信念、信任,或甚至是深刻的記憶。這...是不是聽起來很像我們現在的日常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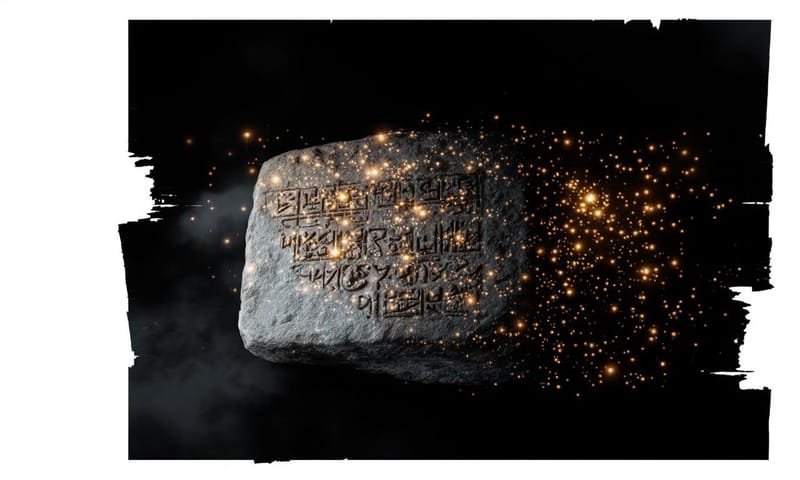
那個「零摩擦力」的答案引擎
所以,伊尼斯的理論告訴我們,每種媒介都透過「設定犯錯的成本」來影響真實。在石頭上刻錯字的成本太高了,所以你會謹慎。但現在的「答案引擎」——也就是 Google 的 AI Overviews 或 PerplexityAI 這些東西——完全把這個公式顛倒過來了。
它們快、免費、隨時都在,而且用一種絕對自信的語氣說話...但同時,它們幾乎不為自己說的話負任何責任。這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傳遞系統所帶來的偏誤:它產生的答案「看起來」像真理,卻可以被無止盡地、悄悄地修改。
這種矛盾非常重要。這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,這是一個哲學問題。
過去,我們判斷一個資訊該不該信,會有很多線索。報紙頭版的標題暗示了事件的緊急性;廣播員沉穩的聲音帶來權威感;就算是一篇部落格文章,你也能感覺到背後作者的風格和立場。但 AI 答案把這些線索全都剝光了,它給你一個乾淨、漂浮在所有資訊之上、沒有出處、沒有情緒的段落。
所以「談判」的比喻才這麼貼切。我們不再是去比較和驗證不同的說法了,我們是在對「系統呈現答案的方式」做出反應。如果它看起來排版整齊、文法通順、很有自信...我們就信了。這過程幾乎沒有摩擦力。

品牌方搞錯重點了,問題不是內容是「脈絡」
說到這個,很多品牌或內容創作者,我自己覺得,他們完全搞錯了挑戰的核心。大家以為挑戰是「產量」。發更多文章、PO 更多文、想辦法讓更多頁面被排名。
但真正的挑戰早就不是內容了,而是「脈絡」(Context)。
大部分公司還在玩那個舊遊戲...追逐反向連結、調整關鍵字、大量生產頁面去滿足那個「排名連結」而不是「解決問題」的舊演算法。這招以前有用,那是因為品牌還能控制整個敘事。你可以寫一些官腔官調、小心翼翼、但其實什麼都沒說的公關稿。在那個時代,你這樣做看起來很謹慎。
p>但在今天這個「答案優先」的世界,你再這樣做,看起來就很像在迴避問題。更有趣的是,你寫的那些內容,不管多好,都會被 AI 撕碎、重組、然後斷章取義地呈現出來。這就產生了一個弔詭的現象:信任感,現在發生在你的內容「下游」非常遠的地方。讀者是在看完那個被 AI 拆解過的摘要後,才「感知」到你值不值得信賴。就算你原文寫得百分之百正確,你也可能看起來完全不可信。
實作指引:所以我們現在到底該怎麼辦?
如果搜尋已經是一場談判,那品牌就不能再用老方法上談判桌了。單純為了發布而發布,並不會讓你更可信。反而,我認為有幾個方向更值得思考。
1. 擁抱「不完美」但完整的答案
我花很多時間在看金融服務業的內容。大部分銀行寫文章,都是為了導流到自己的產品。例如,一篇標題是「Z世代的退稅款該怎麼用?」的文章,如果裡面每個建議都巧妙地把你引導去開他們家的活存帳戶,那你就已經輸了。
不是因為你的產品不好,而是因為你的「答案」不完整。一個真正有幫助的答案,應該要包含所有選項——即使其中一些選項對你沒直接好處。例如,誠實地告訴他,一部分可以存起來(用你家的帳戶不錯),一部分可以考慮投資 ETF(即使你家沒賣),一部分甚至可以花掉去旅行、投資自己。
這種願意提供「完整脈絡」的態度,才能在內容被 AI 摘要後,還能殘留下一絲絲的信任感。
2. 強化「經驗」的信號
AI 很會總結「事實」,但它很難模仿「經驗」。你的內容需要充滿只有第一手經驗才能提供的細節。與其說「選擇一個好的相機很重要」,不如說「我上次在黃昏的河邊,因為相機的 ISO 不夠高,錯過了那隻翠鳥最美的瞬間,從那之後我才知道高 ISO 在低光環境下的重要性」。
p>這種帶有個人感受、失敗經驗、具體場景的內容,更難被 AI 摘要,也更能直接與讀者建立連結。3. 在地化的思考與比較
你知道嗎,伊尼斯是加拿大學者,他從宏觀的歷史角度看資訊流動。但其實這問題,我們在台灣感受可能更深。你看從 LINE 上面每天傳的那些健康謠言,到選舉前的各種資訊戰... 像是「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」這樣的單位一直在提倡媒體識讀能力,但伊尼斯的理論點出一個更麻煩的問題:當資訊的「傳遞成本」和「犯錯成本」都趨近於零,我們的大腦會不會也跟著「懶得思考」了?
這不只是分辨假新聞,這是我們整個認知習慣的改變。所以,當我們在提供資訊時,或許可以多做一步,例如比較美國 FDA 的建議和台灣衛福部的指引有何不同,解釋背後的法規或民情差異。這種「跨情境的脈絡」是 AI 目前還很難做到的,也是建立權威感的好方法。

反例與誤解釐清
很多人可能會覺得:「好,那我以後寫文章就多加一點個人故事,多放一點細節就好了吧?」
嗯,這只對了一半。如果你只是把「增加 E-E-A-T 分數」當成一個待辦事項來打勾,那就又回到舊的 SEO 思維了。重點不是你做了什麼,而是你「為什麼」這麼做。
真正的轉變是心態上的。從「我要如何排名到第一?」轉變為「我的觀點,在被 AI 任意擷取、摘要、甚至曲解之後,還能不能站得住腳?它還能不能為某個真實的人,解決一個真實的問題?」
伊尼斯警告過我們:當速度成為目標,記憶就會成為犧牲品。答案引擎很快,但如果它們抹去了建立信念的過程,信任是無法跟著它們一起規模化的。
長遠來看,人們相信的,從來不是那個排名最高的結果。而是那個在經過反覆檢驗、詰問、比較之後,仍然「站得住腳」的東西。
你最近一次用 AI 搜尋時,有真的懷疑過它給的答案嗎?還是你覺得它看起來「很對」,就直接相信了?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經驗吧!